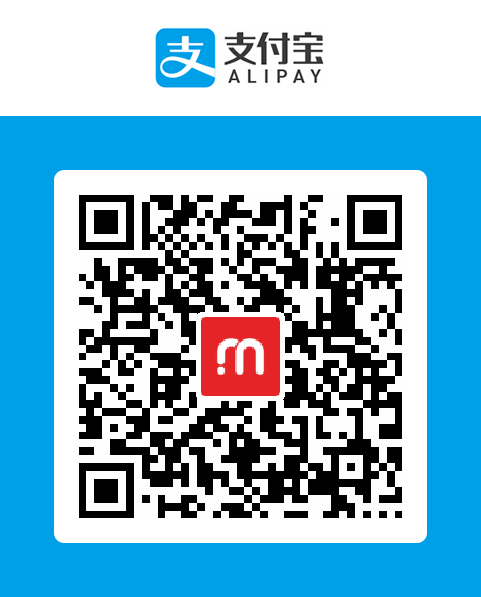由于无论是涉及的群体还是对其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强度均无法确定,因此存在权利保护真空,这就要求国家通过贷款履行公共任务只能是例外情况。
但基本权利首先保障了个体的相对独立性,而不是对国家或他人的依赖性,私有财产权确保了公民个体能够在不受公权力影响的情况下自主规划私人生活的权利,其目的首先是满足财产所有者的私益,而不是实现公益(包括他人私益)。前引13,刘剑文、熊伟书,第206页。

此外,国家征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而如果赠与行为本身就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那么国家征税的空间就会缩小,财产所有者应享有更多选择实现哪一具体公共利益的自由。在流转税[34] 的问题上,与获得收益类似,市场中的商品流通以及商品和非商品的交易一般同样依赖于社会共同体的法治秩序,因此征收流转税也要比征收财产税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强度小。税法通常确定了一个个具体的征税对象,征税对象和过程的多样性意味着立法者要考虑到纳税人实际承受的每一单项税负的正当性。由于在税收问题上并不适用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因此随着社会国征税强度的不断加大,纳税人的纳税自愿性逐渐减弱,[8] 公民纳税义务与私有财产权关系的重心开始从一体性向冲突性倾斜。举例来讲,在我国一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属于财产税范畴,但依照目的划分,其同时又属于再分配税。
换言之,税收法定原则只能使所征之税合法化,尚无法使其合宪化。当流转税在例外情况下无法转嫁给消费者时,企业等于被迫向国家转让部分盈利,由于企业通常还需要承担企业所得税,因此这时征收流转税对企业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强度加大。此外,即使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尚未发现哪个国家或者地区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民事争议,因为这种做法必然违反诉讼制度的内在规律,进而混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自的界限。
关于我国合同效力制度的历史沿革,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以下。该案历经四级法院近二十年的审理,由此产生的法律文书也多达数十份,但当事人的争议却始终无法得到解决,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也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保护。程琥:《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关联案件的诉讼程序衔接》,《法律适用》2009年第5期。也正是基于这一前见,有人就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提出了自认为理想的方案,[19]还有人则提出在当事人就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或者公司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时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受到限制,[20]以尽可能避免民事判决与行政判决不一致的结果。
从已公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看,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旨在完善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交叉时的处理机制,因为在该条文的起草者看来,有些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往往伴随着相关的民事争议。但是,如果将不动产登记视为国家对不动产交易的干预,实质上便是赋予登记机关享有审查交易行为的权力,必然再次引发公权力对私法自治的粗暴干涉。

[14]参见郝振江:《论非讼程序的功能》,《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物权法》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主体是登记机构,其职能是管理不动产登记簿,目的是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以登记的方式公示出来,进而保护物权变动中的交易安全。可见,《物权法》规定的更正登记制度和异议登记制度均表明,在当事人认为登记机关的不动产登记行为有错误时,即应先通过民事诉讼确权,再由当事人申请登记机构办理更正登记,而不是由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总之,如果将用于监督行政权力的行政诉讼制度用于解决民事争议,带来的问题数量将可能远远超过其所解决的问题数量,造成的混乱恐怕不是条文的起草者所能够想象的。
这样一来,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便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可见,至少在当时的不动产登记部门看来,不动产登记行为是一种行政确权行为。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或者地区的不动产登记机关是法院(如德国),有些国家或者地区的不动产登记机关则是行政机关(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不能因为登记机关是法院就认为不动产登记是司法权的行使,也不能因为登记机关是行政机关就认为不动产登记是行政权的行使。在发生登记错误(登记的权利人与真正权利人不一致)时,《物权法》第19条第1款特别规定了更正登记制度,即在登记的权利人作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时,登记机构应当办理更正登记。
此处的起诉,自应理解为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杨建顺:《行政、民事纠纷交叉案件审理相关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09年第5期。

但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关于如何对上述民事争议之外的第三人进行保护,却付之阙如。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不断探索化解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相互交织的审理模式。
尤其令笔者担忧的是,如果修正案(草案)第63条第1款得以通过,则即使今后立法机关制定了完善的非讼程序制度,也可能会带来法律之间的冲突,从而给实践带来麻烦。既然道理如此明了,为何该条文的起草者却置若罔闻,断然釆取一并审理的模式来解决民事争议呢?从说明可以看出,这是因为条文的起草者认为分别审理的模式弊端太多,不解决不行,因此只能采取一并审理的模式。张光宏:《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的性质及审查标准》,《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12期。王达:《房地产纠纷处理中行政与民事交叉问题的正当程序》,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第20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74页。郭敬波:《不动产物权行政、民事交叉案正当程序设计》,《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其一,按照这一方案,一并审理的前提是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提出了一并审理的申请,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一并审理的申请,或者虽然民事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提出了一并审理的申请,但民事争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已事先提起了民事诉讼,如何处理?显然,在当事人没有提出一并审理的申请时,法院无法对民事争议作出裁判,若事后发生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仍然不可避免会出现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织在一起的情形。
由于登记机构并非确权机关,故当事人在发生权属争议时,就只能先通过民事诉讼确权,再持生效法律文书请求登记机关更正不动产登记簿的错误。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
[4]其三,行政诉讼的程序设计不利于对当事人乃至第三人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而在民事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已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下,若另一方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一并审理,人民法院也仍然不得不面临如何处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的问题。
最后,《物权法》规定根据不动产登记簿制作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只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而非唯一合法凭证事实上,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政制度,很大程度上就起源于对政府征税权的限制。
议会担心国王借战争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建立一支常备军或者职业军队,而这很可能使国王推行绝对主义统治。将绕过议会征税的行为定为非法,事实上关闭了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的大门。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颇有吸引力的国家,事实上面临着潜在的深刻危机。当然,即便如此,国王的收入也常常不够开支,不得不征收赋税,甚至包括直接税。
但是,那时的代议不意味着由被代表者选举产生代表,相反,代表或者由官员选择,或者通过抽签决定。他强调,每个人应纳的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任意变更。
注50 征税的原则,应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必需的开支为限,主要是应以保护个人的消极自由和权利所必需的开支为限。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理解充满了歧义。
在这种专制政体下,掌权者统治其臣民就像主人统治其奴隶一样,成为其人身和财产的主人。随着对个人动产征税的扩张,税收离不开代议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前者相当于普通法律,而后者则相当于根本法——宪法。注14福蒂斯丘将政治共同体比作人体,国王就相当于人体的头部,法律相当于人体的肌肉,正像人体的头部不能改变其肌肉一样,国王也不能改变法律。1213年,在圣奥尔本斯召开了针对税收的诉苦大会,不仅贵族和主教参加了集会,而且一群代表们也参加了,这些代表来自王室领地,每个城镇包括四个人和一位行政长官。即便是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也不能随意攫取或者占有人们的财产,事实上,常设议会的议员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迥然不同,因而总是致力于攫取民众的财产,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这样的话,纵然有良好公正的法律设定议员与民众的财产边界,民众的财产依然无法得到保护。
前者意味着国王根据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统治,不经民众的同意就擅自课征赋税;后者意味着国王只能根据民众同意的法律进行统治,未经民众同意不得擅自课征赋税。并且,对于重要事项的制度安排有制约对于次要事项的制度安排的作用。
不停地从纳税人那里攫取财富,将使他们失去创造和生产的兴趣。但是,在亨利二世时代,从对土地征税扩展到对动产征税导致了一个新组织和一种新思想的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法定主义应当受制于税收宪政主义。 三、从税收法定主义到税收宪政主义 17、18世纪之后,代议制政体在许多西方国家确立。